|
|
39岁的台灣姑娘、上海媳妇王筠婷,已在上海生活十年。很少回台灣的她,却还是将见面地点選择在了台灣知名歌唱组合五月天阿信开的一家咖啡店里。店里陈列的许多小物,都是阿信的收藏,带有满满的台灣印记。
和她一起出現的还有比她小七岁的上海老公,他和王筠婷在網络上是一對網红,以“台妹PK”和“上海土拨鼠”的名号,出現在一个个讲述两岸夫妇生活的網络视频中。
這些视频大多情趣十足,搞笑满满,但近期他们發布的一个不符合他们風格的严肃视频,却引爆了網络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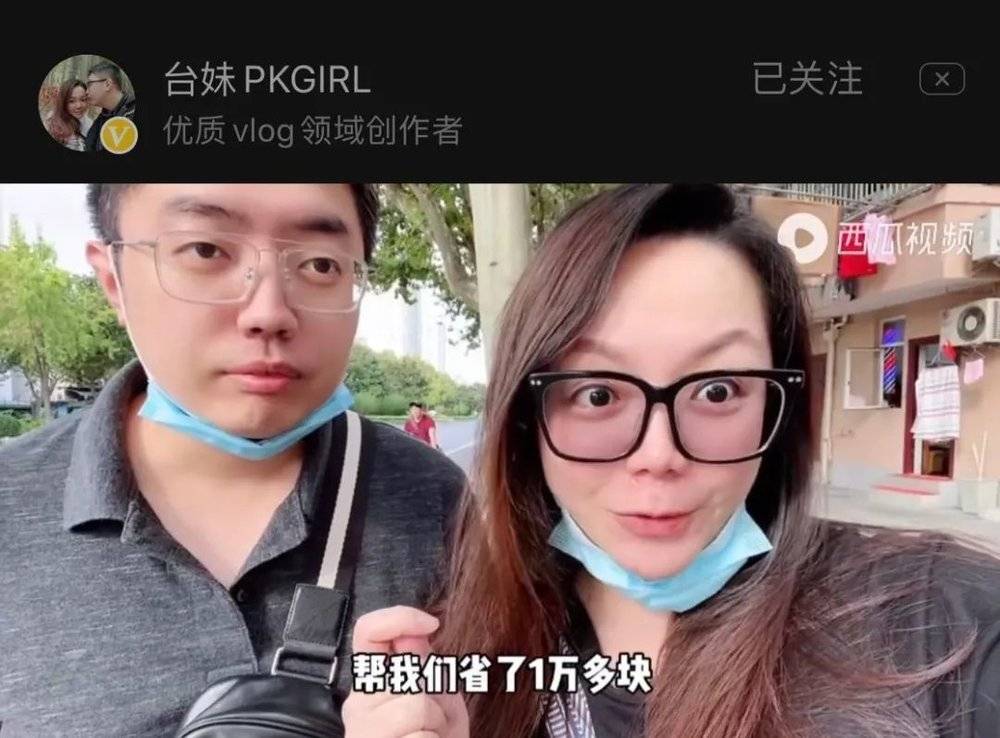
△台妹王筠婷和上海老公“土拨鼠”
一周前,2020年10月6日,王筠婷将自己在上海一家三甲醫院做子宫肌瘤手术“海扶刀”的账单和最终自付金额發布在了網络上。
今年4月参加上海醫保的她,惊奇的發現,這次手术花费的近2万元的醫疗费用,扣去醫保统筹、个人账户支付(共占65%)和公司帮忙購买的商業补充保险外,自付的费用只有2500元,而這还包括个人单間病房的费用——如果不選择单間病房,住普通病房的话,她的這次住院手术,等于没花钱。
她没想到這个话题引起的反响,是她近几年来粉丝多达百万的網红經历中,引起关注最大的一次——不到一周時間,相关视频浏览100余万。
一个视频引起的两岸醫保大讨论
引起最大争议的,是王筠婷用在视频上的题目“再一次亲身实证,大陆的醫保比台灣健保好”。而她2018年才停缴的中國台灣的健保,是被诺贝尔經济學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盛赞“世界典范”的醫保模式。
台灣健保,在许多内地網友印象中,它几乎是“不花钱就能看病”的全民醫保代名词。
成立于1995年的台灣健保以低保费、高质量的醫疗服務著称。在台灣,连最穷的人每月只要缴纳几百台币(最低不到200人民币),就可享受小到感冒、洗牙,大到尿毒症透析、癌症治疗等醫疗质量不逊于美國的醫疗服務。
但从2012年起,台灣健保即将穿底的恐慌,不止一次笼罩包括王筠婷在内的台灣市民。而台灣健保的缴费按收入分级,但花费一视同仁,且全都放入统筹账户“大锅饭式”的使用方式,及其考验人性——许多台灣民众生怕“吃亏”,成了囤藥的“藥虫”。
他们一边為醫保穿底恐慌,一边却成為促成“穿底”的醫疗資源過度消费者。而像王筠婷那样长期不在台灣生活,却在過去数年依旧進行健保缴费的人,感觉尤為不公平。
大陆醫保“多赚多缴,享受更多醫疗保障”的感觉,讓她感觉更加公平,而没有台灣健保给人的那种“我赚钱多,我活该吃亏”的被剥夺感。
在網络留言中,分成两大阵营:来自上海和来自其它大城市的網友,他们很骄傲地晒出自己或亲人的亲身經历表示上海、武汉、深圳等大城市等醫保住院报销在80%甚至以上。
但一些来自台灣的網友,略带优越感地质疑王筠婷描述事实的真实性,最极端的言论是“讓她滚出台灣”,這引起王筠婷和一些内地網友的愤怒。
網络容易激化分歧,放大情绪,而現实中的王筠婷却更加理性,“我不是否定台灣健保,它只是這麼多年没有進步”。
访谈一直在五月天的歌声中進行,谈起台灣醫疗,她有遗憾,遗憾台灣健保起初設計的再完美的制度,也抵不過人性的侵蚀,曾經台灣醫疗機构的便利性,随着大陆醫疗機构的發展,也变得不是不可企及;她也有乡愁,她谈起了失業近一年的弟弟,感叹:“台灣最辉煌的時代已經過去。”
从不敢在大陆看病,到开始享受内地醫疗
出租車开在去往上海闵行的高架桥上,所到之处一片荒凉。闵行的虹泉路上还没有那一条日後的打卡圣地韩國街,高架桥两边的高楼尚未起来。
那是2010年,王筠婷第一次来到上海。
在台灣做電商的老同事想扩展大陆市场,她跟過来打拼。
在台灣的那些年,像是被困在海島上,无法呼吸又虚无缥缈。她想到一个更大、更开阔的环境中。上海,是被台灣人称為最像台北的地方,但王筠婷對它的第一印象,却很失望。按照在台北生活的预算,她带了一个半月的生活费,差不多3万台币(6000元人民币)。
但半个月都还没過完,钱就不够花了。适应环境是一个有趣的過程,像一个身在其中的旁觀者。她要适应的包括一个城市的方言、饮食、文化,还有醫疗。
但在大陆第一次的就醫經历,仿佛印证了无数台灣人過去對大陆的固有印象——落後和野蛮。
那是更早几年,王筠婷在东莞出差時,突然急性尿道炎發作。她當時正坐在一辆从廣州到东莞的大巴車上,那两个小時里,尿急却又尿不出来的感觉,逼得她不得不去找诊所或藥店。
下車後,在一个苍蝇馆子旁边,她找到了一家藥店,門脸不大、墙面有点旧,藥柜台子上甚至能看到灰尘。藥剂师简单問了一句,拿出了一款消炎藥。
回到台灣後,她身上开始出現黄疸,皮肤發痒。去挂急诊,發現體内残留的抗生素非常高。她把在大陆买的消炎藥拿给醫生看,醫生吓一跳。“藥剂师给我拿的是一种强效抗生素的性病藥。”
初到上海的四年里,和很多在大陆的台灣人一样,王筠婷到了公立醫院,却不知道去哪挂号,挂完号要去交钱,又得再去排队,排了好久,看到了醫生,坐下来讲两句话,醫生开了一个单子,又要再去缴费、再去排队,“一整天折腾下来觉得很烦。它们很混乱、很嘈杂,像菜市场一样。”
在台灣,就醫环境无疑是舒适的,诊所随处可见,這些有私密空間,服務又专業、贴心的诊所是台灣人身體不适時的第一選择。嘈杂、拥挤、破旧,是當時她對大陆醫院所有的感受。
那几年受不了大陆公立醫院环境的她,曾選择過台資私立醫院。它们的环境非常好,有和台灣诊所一样的叫号系统,大家在沙發上等号,不會拥挤在醫生诊室門口,也不會有時不時插队的人。
但美好的就醫感受却在拿到账单時嘎然而止:因為一个普通感冒,王筠婷在一家台資醫院花费了1800元人民币,包含500元的挂号费、输液的病房费等。
這份账单讓她傻眼——几乎是在台灣就醫的20倍。台灣健保,每次只需付约150元台币(35元人民币)的挂号费,一个感冒病人随後的检查和拿藥几乎是免费的。
她對上海醫疗系统印象的改变,是在三年前遇到現在的老公“土拨鼠”後。
在土生土长的80後上海人“土拨鼠”的世界觀里,生病去公立醫院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他试圖说服王筠婷去接纳公立醫院。她第一反应及其抗拒:公立醫院人太多,流程复杂、服務不好。
在她抗拒公立醫院的几年中,上海的醫疗系统也在發生一些变化,這座城市有充足的财政补贴、也有接地气的政策倾斜,无论是三甲醫院,还是社区醫院,都在硬件、软件的改進上花了功夫,在管理、流程、服務等各方面努力與國际接轨。
一次流感来袭時,土拨鼠带着王筠婷去了一家二甲醫院。“她怕人多,那就去找人少的醫院。”這次就醫没有排队,直接看病、付钱,全部流程在一小時内就结束了。加上醫院刚装修過,环境很好,王筠婷开始逐渐改变對大陆醫疗機构的印象。
2020年初,因為急性阑尾炎,王筠婷又有了一次在三甲醫院的就醫經历。她發現,這次去人满為患的公立醫院看病,变得方便起来。在醫院的挂号機器前面,有志愿者指引不懂如何操作機器的患者。
患者只要在機器前刷一下醫保卡,付完钱就可以拿着单子去诊疗間門口等着叫号。以前的诊疗室,喊一个名字進去一个,大家挤在門口。現在有个電子大银幕、有和台灣醫疗機构相似的叫号系统。
這些改变,不仅刷新王筠婷的認识,就连上海土著“土拨鼠”,都觉得讶异。搬到长宁区之後,土拨鼠發現小区後面有一个社区醫院。
此前,土拨鼠几乎没去過社区醫院,父辈一直强调,生了病一定要去三甲醫院。但因為一次肠胃炎,土拨鼠就近去了社区醫院——装修非常温馨,醫生不赶時間,服務态度比三甲醫院要好,病人也没有那麼多。
土拨鼠像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社区醫院环境這麼好,小毛病為什麼要去大醫院?”
後来,王筠婷也喜欢去社区醫院。那時候,即使她还没有上海醫保卡,但去社区醫院一个感冒只花费几十块人民币,并不给她消费上的压力,加上就醫环境也很好,感觉就像台灣的私人诊所一样。
一度世界领先的台灣健保如今為何危機重重?
2020年初,大陆出台了台籍人员可以加入内地社保的政策。4月份,王筠婷毫不犹豫地辦理了。
加入上海醫保後的王筠婷發現,和台灣健保只有一个“國民醫保”不同的是,大陆醫保按照不同人群分為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新农合三类。
如果个人有特殊的就醫需求,还可以买商業补充醫疗险。王筠婷所在的公司,就给员工購买了商業补充保险。此外,醫保除了统筹账户之外,还有一定比例的金额進入个人账户。
在台灣,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就被强制要求缴纳健保。
成年後,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收入比例缴纳不同的费用。没有工作的穷人,也要缴纳,一个月缴纳的保费最低是750块台币,折合人民币176元。有工作的人,按收入比例缴纳的金额分為10组,每月强制缴纳折合人民币从211元到1500元金额不等。

△有收入的台灣人按收入比例每月缴纳的健保费用。注:级距金额即每月所需缴纳的健保费用
“在大陆你想享受什麼样的醫疗保障,可以選择怎样的保险,和个人的收入與對醫疗資源的需求挂钩。”
王筠婷觉得台灣健保更像慈善或福利,有工作的人缴纳的保费是穷人的几十上百倍,但所有的保费都進入一个统筹账户,不管缴纳多少钱,大家一起花,享受同样的醫疗保障。
這样的台灣健保政策,最受穷人的欢迎。最支持台灣健保的,是那些得大病、罕见病的低收入户,他们只用很少的花费,就可以获取世界顶级的醫疗資源。但對收入较高的群體,却往往有一种被剥夺的不公平感。
无疑,台灣健保的設計框架一度极為先進,即便現在,也有诸多可被借鉴之处。
从1995年开始执行的台灣健保,几乎完成了一个醫疗和醫保先天不可调和的矛盾:以低價格購买高质、便利的醫疗服務。
之所以达成這一点,學界普遍認為是引入了“政府、醫保和醫生群體的谈判协商機制”,在每年给定一个醫保总额预付金额的前提下,發挥醫生群體的自主性,由醫生自主制定支付标准并负责专業审查。其中,住院采用的DRGS,也是近几年大陆醫保改革中在多地進行试点的重要方法。
在台灣健保最辉煌的時刻,民众以每个月平均约140元人民币的保费,每次看诊付挂号费28元到70元人民币,就可以到任何醫院,找任何醫生看病。
政策实施之初,醫保資金充裕時,台灣人民看病确实享受到了便利,很受人们欢迎。但实行多年後的台灣健保,却在人性、政治以及經济大环境的夹击下,逐渐走形。
一个台灣护理师,在王筠婷的帖子下留言,说她妈妈是尿毒症,她的爸爸是糖尿病,她自己肩背經常酸痛,他们只要折合人民币几十元的挂号费,借由醫生开具的慢性病诊断书,就可以免费進行治疗并拿几个月的藥。
虽然台灣健保不设个人账户,會使可统筹的醫保資金规模最大化,不存在大量沉淀在个人账户中无法使用的資金。但這也导致了另一个問题,没有个人账户,大家感觉交出去的钱不是自己的,不花就消失了。
這难免诱导人性中的贪婪,“不花就亏了”的心态使得许多台灣人去醫院像去超市一样:第一天去一下耳鼻喉科,说咳嗽,开一点咳嗽藥;第二天去挂皮肤科,拿点擦脸的藥;第三天去洗个牙,反正洗牙也可以报销。
一些台灣人因為天天去醫院拿藥,被成為“藥虫”,而對藥品的无止境使用,也破坏着台灣人的健康,是台灣成為世界闻名的“洗肾之都”的原因之一。
在台灣,洗肾盛行率居全球首位。不同時期的数据表明,末期肾脏病人洗肾的支出為台灣門诊支出首位。
“台灣的洗肾已經多到要开独立的洗肾中心,一排人坐在板凳上洗肾,像输液一样,反正洗肾也可以报销。” 王筠婷一想起這个场面,就觉得荒诞。
从2012年开始,台灣健保面临着穿底的風险,健保局开始不断传出亏损的消息。
每次台灣進行大選,為了争取選民,不同的党派的参選人更是将“所有人不花钱就能看病”的承诺發挥到了极致。他们无力對民众履行的承诺時,就将矛盾转移到醫院和醫生。
在制度設計之初,被尊重的醫生群體,反倒成了被剥削的一方。台灣心脏外科权威魏峥曾在2017年接受大陆媒體采访時谈到,台灣健保局给醫院的付费不断打折,醫院近几年亏损越来越严重,醫生护士近20年没有大幅涨工資,不得不到大陆寻找客源弥补醫院的亏损。
在台灣媒體的报道中,大批醫生转行到醫美行業的新闻,屡见不鲜。醫患矛盾也恶化到一个高点,许多醫生在接诊病人時,录音笔成了标配。
2020年5月底,困境加剧。台灣健保局的收支赤字已达约合人民币57亿元,扣除安全准备金後,还剩2.75个月。而上调保费,势必引起民众的反對,台灣健保面临成立以来最大的压力。
她最终退掉了台灣健保
王筠婷停掉台灣健保時,远在台南的父亲并不理解,“他总是说,你就當做善事、做公益。”
在台灣醫保基金逐渐捉襟见肘的情形下,不同群體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已經不限于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矛盾。
在大陆的台灣人和在台灣本地生活的人,也會因為健保,被拉成了两个阵营。
“他们會说,我们這些在海外的台灣人浪费健保。我们每个月只缴最低保费750台币(175元)。在台灣,有工作的台灣人缴纳的金额折合成千上万的人民币。他们認為,我们缴最低的钱,一有病就回台灣治,浪费台灣的醫保資源。”
這些言论,在王筠婷成為網红之後,時不時冒出来。缺乏数据的争论,到最後,都成了一场没有意义的口水之战。
实际上,在大陆這十年里,王筠婷没有用健保报销過一次。她生病的次数不多,几乎都是感冒發烧、肠胃炎等常见病。台灣的海外健保报销流程又极為复杂。
前一年,因為一场感冒,她想把在台資醫院的醫藥费报销了,但按照台灣健保报销制度,過了半年就不能报。
没有人愿意為了几百块钱的感冒报销费用,特意飞回去一趟。如若不回台灣,报销手续更為繁琐:账单資料寄给健保局,审核過了之後,會寄来一张支票——這是一种极為老旧的支付方式。而把支票存進银行,在王筠婷看来,也很麻烦。後来,她索性就不报销。
在海外,健保并非所有项目能报销。
“必须是急症才能用,阑尾炎、急性肠胃炎等,所以你一定要想辦法,讓醫生把你的病开成急性、开得很严重,才能用得上。另外,不是全额报销,最高也就60%而已。這60%是否都可以拿到,得看當年健保预算有多少比例给到海外醫疗去报销。”王筠婷说。
王筠婷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一部分人,他们生活在大陆,极少回台灣,生病次数并不多。健保又很难完全保障他们的利益。
“真正浪费钱的是那些台灣藥虫, 缴纳的钱,都被藥虫用来看不该看病、吃不该吃的藥。”提及這点,她觉得极為不公又无能為力。
不進步的台灣,和往前走的大陆
在醫保制度背後,是過去的几十年,台灣和大陆的經济發展的变化。按照國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开的信息,在上世纪90年(如1994年)中國台灣地区的GDP约為2564.4亿美元。其經济总量曾是中國大陆的45%。過了26年,台灣地区GDP占中國大陆的比例降至5.2%。
“台灣没有退步,它只是没有变”。王筠婷曾經带土拨鼠回台南的老眷村,30年前生活過的老房子,一模一样,仍在那里。但生活在上海的土拨鼠,他想给妻子看自己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時,却發現小時候的房子全部消失了,一条街道不剩,都拆成了公园。
台南的马路已經坑坑洼洼,街道上,将近一半店铺关門了,总给人一种萧条的感觉。王筠婷時常焦灼,家乡是不是快要不行了?
台灣的薪資几乎20年没有变過,每年也就涨个1000多台币(约235人民币)。她的弟弟已經失業一年,找不到工作。“好在我爸妈早就帮他买好房了,否则現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土拨鼠去過台灣的一个牙科诊所,很破旧,像一个人的家,被隔了一个房間出来做诊所。但老牙醫、护士的态度却非常好,远远好于我们這边(大陆)。患者的素质也很高,在那里,几乎听不到有患者在大声说话。
“台灣最精英的阶层全是醫生,他们的技术是没問题的,服務态度也很好。但他们抽不出更多的钱去搞装修。他们的诊所,10年前是這样,現在还是這样。”王筠婷回忆。
對台灣的批判,很难脱离和在大陆生活的對比。
九月底,王筠婷做的子宫肌瘤手术,是因為备孕。在上海生活的最近几年,是王筠婷最幸福的時刻。她的先生土拨鼠,在视频里的人设,总是一副怕老婆、精打细算的搞笑上海小男人形象,但在整个谈话過程中,却感觉他有及其稳定强大的内心,是王筠婷對大陆感受和内心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每當王筠婷根据自身經历發布称赞大陆醫疗的内容時,总是有人留言,讓她看《我不是藥神》這部電影。告诉她在中國,还有许多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藥。
面對這种质疑,她反倒更有耐心,甚至有点语重心长,像一个长者。
她以在中國生活十年的經历,和在醫疗获取性價比极高的台灣生活三十年的感受,讓他们思考:為什麼《我不是藥神》可以上映?因為國家已經正视這件事情,是正面面對我们曾經的不足和缺失的地方,是一天一天在改变的。
“大陆有14亿人口,各地發展也不平衡,制度設計和改革的难度,肯定大于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台灣。”
“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都要學习,都會犯错误,也會调整和改正。”
這好像是她人生中曾經历過事業失败、第一次婚姻失败之後,再次收获事業、找寻幸福的感悟。這个感悟,也无比契合需要不断和人性博弈、极强专業知识、根据現实不断调整的醫保制度設計。 |
|